男女主角分别是谢玉琰王晏的女频言情小说《四合如意 全集》,由网络作家“谢玉琰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二老太爷的小厮,在马车前听了声吩咐,就握着名帖匆匆离开。马车继续前行,到了杨家门口,杨骥先弯腰下了车,然后转身将二老太爷搀扶下来。脚刚落地,二老太爷盯着迎出来的管事,沉声道:“怎么回事?”管事先看了看门口的军卒,眼睛中闪过几分忌惮:“三房六郎媳妇,告一个郎妇偷盗家中财物。”二老太爷显然对管事的禀告并不满意,都是囫囵的消息,里面有什么内情却没说出半分。“祖父别急,”杨骥道,“既然是内宅的事,问问二伯母就能知晓。”他离开家的时候,何氏满脸都是血迹,神情惶然,他觉得何氏搅不起风浪,这才放心去寻祖父。以他对何氏的了解,何氏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,现在突然冒了头,定是有什么理由,更该弄清楚的是,何氏是听了谁的话,将管事大权给了那谢氏。二老太爷皱眉...
《四合如意 全集》精彩片段
二老太爷的小厮,在马车前听了声吩咐,就握着名帖匆匆离开。
马车继续前行,到了杨家门口,杨骥先弯腰下了车,然后转身将二老太爷搀扶下来。
脚刚落地,二老太爷盯着迎出来的管事,沉声道:“怎么回事?”
管事先看了看门口的军卒,眼睛中闪过几分忌惮:“三房六郎媳妇,告一个郎妇偷盗家中财物。”
二老太爷显然对管事的禀告并不满意,都是囫囵的消息,里面有什么内情却没说出半分。
“祖父别急,”杨骥道,“既然是内宅的事,问问二伯母就能知晓。”
他离开家的时候,何氏满脸都是血迹,神情惶然,他觉得何氏搅不起风浪,这才放心去寻祖父。
以他对何氏的了解,何氏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,现在突然冒了头,定是有什么理由,更该弄清楚的是,何氏是听了谁的话,将管事大权给了那谢氏。
二老太爷皱眉:“叫你二伯来回话不是更好?”
杨骥目光一闪,他看了看门口的军卒,脸上是异样的神情,虽然没开口反驳,却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。
二老太爷脸色更是难看,骥哥儿这是怕老二那畜生与贺檀勾结。
眼下的乱子,可能根本就是他们演的一出戏。
一个刚刚进了杨家的女子,怎么拿到的管家权?她对杨家一无所知,怎么敢去抓郎妇的错处?还惊动了巡检衙门。
二老太爷咬牙:“真是好大的胆子。”这是要拿整个杨氏一族去换前程,怪不得能做了坊副使。
既然对杨明经有了怀疑,自然要先试探何氏。
“家中是不是有官爷上门?”杨骥没忘记问管事。
管事立即道:“是贺巡检,人正在堂屋里。”
猜测被证实,杨骥面容更加严肃:“你去回禀一下贺巡检,就说老太爷刚回来,换了衣服就去拜见。”
管事应声。
这都是为了拖延时间,等二老太爷出来见贺檀的时候,也弄清楚了大致的情形,小厮去请的老者也到了。
大梁乡、坊不再设三老,但当着永安坊所有老者,贺巡检也得给几分颜面。
杨骥希望这事能顺利解决,家中能安然无恙,还不会得罪贺檀。
要知道贺檀背后可不止是贺家,还有显赫的王氏。
二老太爷和杨骥径直奔向主屋,人还没走进院子,就看到老太太屋里的管事快步走来。
二老太爷看到管事脸上惶恐的神情,立即动怒:“做什么去?”
管事妈妈急切地道:“老太太突然晕厥了,怕是得了内风,正要去请郎中。”
杨骥目光闪烁,他记得这个管事是祖母身边最得力的,平日只安排别人差事,现在祖母病着,她怎么会不守在祖母身边?
“其余人呢?”杨骥道,“怎么妈妈亲自出来?”
管事眼睛通红:“家中出了乱子,老太太吩咐管事去向六郎媳妇问情形,却被六郎媳妇行了家法,到现在也不知死活,老太太又让大丫鬟去要人,结果也被拿下行了杖刑。六郎媳妇还放出话来,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的从犯。”
“老太太就是因此被气得晕厥。”
“将那个谢氏给我叫来,”二老太爷瞪圆眼睛,“我要向她问话。”
管事苦着脸:“花厅那边关了门,任谁也叫不开。”
“这是杨家,”二老太爷道,“任她一个疯妇无法无天不成?”
管事抿了抿嘴唇:“奴婢去问了,六郎媳妇说……她是管家人,手中握着族里给的腰牌,就得打理好内宅中馈,现在查出大事,她得将一切弄清楚,带着杨氏渡过难关,在此之前,花厅只进不出。”
二老太爷道:“你们就听她的?”
管事目光闪烁:“二娘子抱病,方坊正来了家中叫了二老爷过去,花厅门口还有军巡卒守着,我试着给了银钱打点,军巡卒却不肯收,还要治我们贿赂之罪。”
杨骥插嘴道:“二伯去过花厅吗?”
管事应声:“去了,大约两刻不到就出来了,也没能带出六郎媳妇。”
为什么杨明经就能出入花厅?二老太爷看向杨骥,果然就跟他猜测的一样,闹事的根本不是谢氏,而是杨明经。
“这是出了家贼。”二老太爷看向杨骥。
杨骥再也没法维持表面的平静,脸色也变得阴沉,他扭头去看身边的随从,随从点头转身向外走去。
杨骥仔细思量,就算二伯下手,只要别摸到北门外的庄子上,就什么也查不出来。
那庄子该是无人知晓的。
想到这里,杨骥眼皮突然一跳。
……
杨明经和方坊正正在说话,下人来禀告:“二老太爷回来了。”
杨明经不禁深吸一口气。
方坊正见状道:“定是知晓家中出了事,你要不要过去说话?”
杨明经打断道:“贺巡检在这里,还是要先去见巡检大人。”
方坊正看着满头冷汗的杨明经:“你这是怎么了?”
杨明经紧绷着后背,一股凉意慢慢从脚底向上爬,如同趴了只千足蜈蚣,让他整个人因恐惧而战栗。
明明从花厅出来许久了,却还是无法从谢玉琰的问话中回过神。
再看看面前的堂屋,那道门好似通往鬼门关。
可他就是再不愿意,也得走进去。
“那就走吧,”方坊正催促,“别让巡检等急了。”
方坊正先行一步,杨明经木然地跟随,但是每走一步,脑海中闪现的都是谢玉琰平静的面容。
他本意是阻拦谢氏继续生事,谢氏却淡然地问他:“二伯可是想清楚了?无论什么结果,二伯可都能承担?”
不过就是杨氏一族内的争端,他一个族长还不能处置?
可是接下来谢氏的话,却让杨明经几乎吓得丢了魂儿。
“二伯可知大名府为何突然设了巡检衙门?又让贺巡检前来?”
这个杨明经自然知晓,杨氏只是个小商贾不假,但大名府的达官显贵也肯给他们一碗饭吃,自然不缺消息来源。
贺檀是来查武将与商贾勾结之事。
谢玉琰接着道:“朝廷如此大动干戈,总要有个回音,贺巡检也是如此,来到大名府就要做出些事交差。”
“抓一个寻常的商贾,不足以应对朝廷。”
杨明经听到这里,还不明白谢氏的意思。
然而后面的话,却惊得他魂飞魄散。
“不过一个身兼坊副使的商贾被抓出来,应该可以佐证大名府衙署失察失职,从而佐证朝廷设立巡检衙门是对的。”
谢氏的神情明明没有变,只是淡淡地瞧着他,但杨明经却感觉那道视线如同利器,正好戳进他的胸口。
然后谢氏的嘴唇再次开启:“坊副使不够的话,那就拔擢成坊正使再抓。”
杨明经脚下就是一软。
“二伯,”谢玉琰道,“听说方坊正年纪不小了,旧疾缠身,也该卸任坊正一职,二伯可能又快升迁了。”
说完,她将手中纸笺递给杨明经:“二伯看看吧!”
杨明经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拿起那些纸笺,又怎么一张张从头看到尾的了,他只知道那厚厚一摞纸在他手中如同一块烧红的木炭,灼得他生疼。
杨明经恍惚回过神,但映入他眼帘的却是方坊正花白的头发。
从前他心里一直盼着方坊正卸职,可现在他恨不得跪下祈求神佛,让方坊正康健、平安,再多掌管永安坊几年。
杨明经晃晃悠悠地走着,迈过门槛时,脚下失了准头,登时被绊了一下,整个人向前摔去。
狠狠扑在地上的杨明经,顾不得疼痛,他只是恐惧异常,这一跤好似个预兆……
从此,他跌入地狱魔窟,再也不得翻身。
张氏眼睛中满是担忧,可当对上谢玉琰那平淡的目光时,心头的慌乱莫名地去了大半。
谢玉琰坐在椅子上,拿起了郎妇递来的名册。
郎妇抿了抿嘴唇,她是旁支族人,夫君与族长同辈,当年家乡灾荒,夫君一家拿着家谱前来投奔,吃了族中的饭食才活下来,她也是夫君一家收的童养媳,从小就随了夫姓。在族中这些年,杨氏手脚勤快,口齿伶俐,才会在族中掌些事务,这次也被众人推过来向谢玉琰回话,希望大娘子发火的时候,她能靠着巧嘴,平息些大娘子的怒气。
杨氏正琢磨要如何说话,谢玉琰已经道:“让她们将在族中做过什么活计都写下来。”
这是……没嫌弃人少?
杨氏和郎妇们有些惊诧。
谢玉琰道:“接下来有些事会交代给大家去做。”
片刻后,众人回过神,大娘子这是在选人了,最先投奔过来的人,自然能分到好的活计,不管大娘子要做什么买卖,一向是有用的人才能在族中立足。
“是,大娘子。”郎妇应了。
根本不用她们说话,或是出什么主意,换句话说,她们按大娘子的吩咐,尽心尽力将事办好,无论出什么结果,大娘子都不会怪罪她们。
既然有了章程,后面就好办多了。
将自己这些年的职司写好的郎妇,一个个入内,谢玉琰问了几句话,就让人退了下去。
杨氏在一旁听着,心中暗自惊叹,大娘子三言两语就将这些人都摸透了,有人给账房打过下手,有人在小库房管过器物,有人擅长管杂事,一张纸上说的明明白白。
众人都有什么毛病,虽然没在纸上写着,只要问一句:“为何卸职?”也就都清楚了。
接下来,三个郎妇要跟着账房熟悉账目,不能与账房先生那般,将整个族中的银钱进出都算清楚,但也要能支撑一个小铺子的银钱流通。
谢玉琰又选出三个郎妇:“杂物库出了差错,族中重新盘点外库的货物,你们三个就跟着一起,将库中的问题都记下来。”这样就能更快熟悉库中事务。
还有三个郎妇,需要将族中各人做的职司都问仔细,还要摸清外院和内宅的下人如何调动、轮换。
谢玉琰单独留下杨氏,让她打听族中各种消息,九个郎妇在做事时,遇到的问题,都要先去寻杨氏,然后再由杨氏禀告给谢玉琰。
谢玉琰道:“她们九人中,有谁觉得办不好我吩咐的差事,随时都能退下来。”
杨氏试着问:“退下来的意思,就是不再用了?”
谢玉琰道:“族中不养闲人,不想做差事的,就让她们带着银钱回去,着实没有能力做好的,日后还会分派她别的活计。”
杨氏明白了。虽然她们还没着手去做事,但已经想到会是什么情形,族中管账、管库房的人都有定数,突然加派人手前去,定会被人嫌弃、猜疑,原本的管事怕被顶替差事,必然想方设法处处为难。
但是,只要能熬过去,将来就可独当一面。
别以为这些郎妇,被她们劝说几句就肯前来,她们大多都是在何氏那里得不到重用的。
比如那三个被分去账房的,原来的差事办的好好的,都是被何氏的亲信替换了,现在重新得了机会,自然要用出浑身解数,向大娘子展露自己的本事。
大娘子这番用人的手段,何氏哪里能比?
派出去的人,会愈发对大娘子有信心。
更别说,此举会让族中人心惶惶了,杨氏猜测明日会有更多人来投奔,但差事就这么多,后来的人只能分她们剩下的。
将人都打发走了,张氏忙端了茶水给谢玉琰,跟在谢玉琰身边看的多了,张氏也越来越泄气,许多东西看不透也学不会,人与人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,当年老爷主张族中子弟读书是对的,多读书才会有眼界。
谢玉琰将徐氏送给她的竹篮打开看,里面放着一双羊皮做的手笼。手笼的针脚缝的密实,可见徐氏用了不少心思。
张氏道:“我也准备些吃食给高家送去。”
“娘不用着急,”谢玉琰道,“明日他们会来,到时候再给不迟,这么快就将东西还回去,高家还会以为我们不愿与他们来往。”
帮高家将状纸递去衙门,徐氏就能收到杜家赔偿的银钱,这才是高家真正需要的。
谢玉琰就是要借机在坊内推广诉讼,六十年后的大梁,百姓们请讼师很是寻常,这种事多了,百姓们不再惧怕上公堂,不少民众的冤屈得以伸张。
现在虽然有了代写讼状的书铺,民众们大多不敢走进去询问,恐怕给不起润笔的银钱。只有真正推行开,大家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好处。
谢玉琰正思量着,只听张氏“咦”了一声:“怎么有只狸奴?”
话音刚落,谢玉琰膝上一重,一只狸奴跃入她怀中。
通身灰棕色相间的皮毛,只有脖颈上一圈毛发略微发黄,正是她在巡检衙门遇到的那只,没想到它会一路跟着她到了杨家。
谢玉琰将手放在狸奴头上,熟练地抚摸起来。
前世她宫中也养了狸奴,宫中最多的就是这种灰棕色。她会格外偏爱这样的花色,只因她人生第一只狸奴,便是这般模样。
她四岁时,差点在庄子上走失,只有小狸奴陪着她,可惜谢家人再寻到她时,她的狸奴却不见了,她为此伤心了许久。家里人都说,林中有抓人的山魈,狸奴替她挡了山魈,她才能安然无恙地归家。
怀中狸奴乖顺地舔着谢玉琰的手指,然后将下颌搭在了谢玉琰手腕上,一双大大的眼睛定定地瞧着她,竟像是在外浪迹许久,终于寻回了家。
张氏仔细瞧了瞧:“这像是被人养起来的,不知会不会有主家来寻?”
谢玉琰压了压狸奴的爪垫,几根尖利的爪子立即露出来:“应该是养在外面的,等它耍够了,就会自己归家。”
狸奴这时晃了晃头,仿佛是在反驳谢玉琰的话。
张氏笑道:“我去给它找些吃食来。”
谢玉琰的手轻轻攥着小狸奴的爪子,拿起桌上郎妇写的纸笺来看,很快她听到膝上传来轻柔的呼噜声。
比起三房的闲适,何氏房中一直不得清静。
“那谢氏将投奔过去的郎妇,安插在账房和库房了。”
这几个人就像丢入湖中的石子,一下子起了波澜。
何氏揉着额头,从昨晚开始,她的头疾就愈发严重了,疼得她睁不开眼睛,偏偏谢氏半点不消停,各种消息不停地送到她跟前,催促着她去处置。
“让她们别慌,”何氏道,“没有错处,谁也不能抢了她们的差事。”
可是光凭这一句话,无法安抚人心。
何氏只得强撑着起身,将账房的几位先生都唤来嘱咐一番,重新核对外院几个库房的账目,总之不能让谢氏再找到把柄。
这些都是她多年的心血,绝不能落入谢氏手中。
谢玉琰打发那些郎妇前去,说好听的是跟着学管理事务,那些本事学来做什么?总不能她一下子变出几个铺子,让那些郎妇去管。
杨氏族中斗来斗去,抢夺的手段,何氏比谁都熟悉。
“拿些东西给几个长辈,”何氏嘱咐杨申,“我掌家这些年做的如何,他们应该清楚,谢氏这样胡乱施为,只会让族中越来越乱。”
“现在不得已要用她,日后中馈还得回到我手上。稳住他们,不要他们起别的心思。”
杨申点头:“那谢氏将族中弄成这般模样,大家都看在眼里,中馈事务上,是娘做的好,还是谢氏做的好,是明摆着的事,娘只管安心。”
何氏擦掉额头上的冷汗,重新躺回床上,事无巨细都安排好了,可她一颗心却依旧提在嗓子口,总觉得自己做的这些……根本防不住那谢氏。
她用了这么多年才得到族中长辈认可,谢氏总不能短短几日,就扭转情势,让大家改了主意?
说到底,都怪那吃里爬外的于氏,否则她怎么会如此艰难?
……
这一日过的格外慢,王鹤春抬起头看了眼沙漏,目光落在那装着饭食的小碗上。
“呦,真没回来啊?”贺檀撩开帘子走进门。
王鹤春的那只狸奴,每日都要跑出去,但是无论在哪里,它都能准时回来吃东西,今天却不寻常……
该不会这次是真的跑了吧?
那只狸奴对王鹤春来说,可不一般。当年王鹤春将狸奴抱回来的时候,只说林中捡来的,当时贺檀也没在意,直到王鹤春酒醉时,无意中透露出几句言语,仿佛与他那次“遇仙”有关。
所以,这狸奴无论如何都不能丢。
童忱正在胡乱琢磨着,感觉到一道目光落在他身上,紧接着他心里打了个冷颤,彻底回过神来。
好像方才他在想些什么,王……公子都知晓似的,童忱清了清嗓子,正要开口说话。
旁边的杨钦先一步,躬身向童忱行礼:“见过先生。”
“他叫杨钦,族中行九,住在大名府永安坊,”王鹤春道,“胞兄是阵亡的将士。”
杨钦心中一阵紧张,恐怕这位童先生会问他,家中都是做什么的。
去年,母亲去找过临坊的秀才,请秀才做他的西席,秀才听说杨家是个商贾,立即就拒绝了。
杨钦正胡乱想着,童先生的声音传来:“可识字?”
杨钦道:“母亲教过一些。”
既然要做先生,自然要有些威严,童忱道:“从明日开始,每隔两日来这里旁听。”
“虽是旁听,我交代的课业却都要完成,否则就不必再来了。”
正式拜师之前,都要有考较,若是不能让先生满意,先生自然不会再教他,杨钦好不容易才得了读书的机会,别说一点课业,就算要求再多些,他也能做到。
杨钦再次弯腰:“是,先生。”
童忱看向小厮:“带着他四处看看。”
小厮应声,领着杨钦离开,童忱板起的脸孔立即松懈下来:“公子,我们去屋子里说话。”
两个人进了门,不等王鹤春开口,童忱一揖到地:“人前怠慢之处,还请公子恕罪。”
王鹤春坐下道:“本是我让人知会的你,要遮掩身份,不必思量太多。”
童忱恭敬地奉茶给王鹤春:“公子来大名府,可是有重要的事要做?”否则也不会隐去姓名,藏在巡检衙门。
王鹤春点点头:“个中原因,还不能与你说。”
童忱明白:“只盼着能有机会为公子效命。”
王鹤春点头道:“等局势明晰一些,自然让人知会你。”
童忱心中欢喜,其实之前他也曾随王鹤春做过事,就是不知晓哪里做的不对,突然公子就不用他了。
到现在他也没能弄明白。
“公子稍坐,我还有样东西送予公子。”
童忱说着匆匆忙忙出了门,片刻之后去而复返,手中多了一本书册。
“公子瞧瞧,这是新印出来的《神童诗》,”童忱颇为惋惜地叹口气,“公子少时还有不少诗句没能流传,否则……”
“印了多少?”
不知是不是错觉,王鹤春的目光似是慢慢变得幽深了。
童忱心中一惊,忐忑道:“二百册。”
“多少?”王鹤春又问。
童忱小心翼翼:“淮南有两个商贾……格外喜欢公子的诗句,每人又印了两百册,说好只给族中子弟看。”
王鹤春没有说话,童忱却感觉到气氛愈发低沉,他额头上的冷汗也越来越多,于是没有等王鹤春再问,他就竹筒倒豆子地说了。
“还有福建来的人……这次是读书人,给书院买了一百五十册,再就是成都的一位员外,要给族中子弟启蒙用。”
童忱说着,从旁边拿出一本账目递给王鹤春:“卖的银钱,都给西村的孩子们置办了笔墨,公子看看。”
“赚了不少银子,”童忱道,“若是再印几百册,也能卖得出去。”
“够吗?”王鹤春忽然淡淡地道。
看了账目后,公子的心情似是好转了,想到这里童忱仗着胆子:“不太够。”
“其实那书局的东家与我说,他们更喜欢看公子小时候的那些事,若是能印出来,定然能卖出许多。”
“你想写出来卖?”
淡然的声音传来,童忱下意识就要点头,毕竟他们穷,若是能多赚些银钱,写点趣事儿而已,也没什么,不过他很快回过神,即将脱口而出的话,也被他吞了进去。
童忱慌忙改口:“没想写,公子小时候的事,我……如何能知晓?”
王鹤春抿了口茶,彻底没有了在衙署时的温和,整个人变得格外冷峻,目光却愈发的平静:“不知道好,知道太多的人,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”
想想外面流传的那些书册,八成都与眼前这个人有关。
“我不想带着一群孩子玩耍遇险。”
“也不想在老大人与同僚一筹莫展时,一语惊醒梦中人。”
“更不想对着鸡鸭说话,对牛弹琴。”
童忱不禁吞咽一口。
王鹤春放下手中的杯子,站起身,走到童忱面前。
童忱盯着那黑色的靴面。
“我没有,离开家去寻什么仙人。”
“没有,绝食七日,要与那仙人一见。”
童忱摇头:“没有。”
王鹤春接着道:“更没有与那仙人有簪花之约,非卿不娶。”
童忱摆手:“没有,没有。”这个一定是没有,他绝对不会再与人说,许多年前,他在山中捡了饿得奄奄一息的王鹤春,若这都是真的,岂非是告诉大家,王……公子被人骗了?
大梁大名鼎鼎的神童,怎么可能被人骗?
王鹤春走到门口,他忽然指向外面:“那孩童一家与我无关,更非我留在外的子嗣。”
“若是让我看到一点,我与那杨家人之间的只言片语……”
王鹤春没有继续说下去,但童忱旁边的窗子突然无声地打开了,一阵凉风吹入童忱的领子,就好像柄利刃,送入了他的喉咙。
“不敢,不敢。”童忱拼命摇头,他再也不敢动那样的心思。
“好好读书,”王鹤春道,“带着你这些弟子,早日考中进士科。”
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心思,以童忱的才学,早就考中了。
王鹤春踏出屋子,就看到候在外面的杨钦。
没有再多停留,王鹤春到了门口翻身上马,再次向杨钦伸出手,不过这次杨钦只是躬身行礼道谢。
王鹤春道:“不与我一同回去?”
杨钦摇头:“嫂嫂还交代我,要带回些东西,就不劳烦王主簿了。”
看着杨钦那小小的背影,王鹤春嘴角弯起露出一抹笑容,然后带着小厮也驱马离去。
……
永安坊,杨家。
杨二老太太昨日被气的厉害,晚上连饭都没用,就早早歇下了,早晨起来仍是没有胃口,何氏在旁边劝说了好一阵,杨二老太太才答应吃些乳酪。
洒了红果碎的乳酪吃下肚,二老太太的心情也跟着好了些,正要让何氏盛一碗肉羹来,就瞧见管事急匆匆进门。
二老太太心头“咯噔”一下。
昨日老太爷训斥的话还在耳边,告诫她莫要再闹出事端,否则她那心爱的小儿子,可能就没法回来了。
掠卖人口在大梁是重罪,掠卖人死罪,买主至少要杖刑,判的重些就是配役三年,无论哪一个,杨明山都受不得。
所以昨日何氏提议将小库房钥匙给三房,二老太太没有犹豫就答应了,一来能稳住三房,二来等这阵风过去,就将三房处置了。
可这才过去一晚上,难不成就又闹出事端了?
管事匆忙开口:“老太太,三房请了两位讼师来,门房拦不住,现在……人已经进了院子。”
二老太太耳朵里一阵嗡鸣,那谢氏真的请讼师了?真的要状告谢家?
“老二呢?”二老太太招手,“快让人去喊老二,他不是想了法子吗?怎么没用处?”
请一个讼师还不够,居然叫了两个上门。
二老太太瞪圆了眼睛:“快点……想法子。”要是再任由谢氏这么闹腾,恐怕等不到老四回家,她就要被气死了。
……
杨家大门口。
谢玉琰站在那里,看着两个讼师跟随张氏去往三房的住处。
刚刚门口这样一闹腾,又引来不少邻里围观。
有人忍不住道:“六哥儿媳妇,你们请讼师做什么?没有禀告谢氏族中吗?怎么闹将起来了?”
谢玉琰瞥了一眼不远处的管事:“诸位邻里不要误会,有些情形家中管事可能不知晓,才加以阻拦。”
“昨日族长已经答应帮我向谢家讨还公道,这些讼师就是登门为我写状纸的。”
郑氏这边喊一声,那边几个妇人立即应喝。
藕炭烧的火候正好,热水已经提前煮沸了几锅,滚烫的水送入提前刷好的大缸中,又将冷水倒入锅中继续烧,屋子里一时热气腾腾。
“将几个炉子摆出去。”
几人挪动着泥炉摆在铺子外,向里面夹入一块烧好的藕炭,再在上面放置只陶锅,里面舀满了水,很快就煮得热气蒸腾。
“这……能不能有人来?”
陈窑村的妇人冒出一个头向外张望,她着实不明白,为何大娘子吩咐将泥炉放在铺子外。
一个泥炉里面至少放两块藕炭,就在外面这样烧着,不都浪费了?
妇人心疼的不得了。
他们不在外面吆喝,只放些泥炉又有啥用?
“总会有的。”郑氏坚信谢大娘子。大娘子心中很有思量,才短短几日,她就习惯了听吩咐做事,铺子没开之前还担忧,现在铺子开了,忙碌眼前的一切,心反而静了下来。
妇人又羡慕地看了看不远处那些热闹的铺子,喃喃地道:“人可真多,啥时候我们也能似那般?”
郑氏道:“莫想别的,快去干活儿。”
……
一家新开的布行外聚满了人,伙计卖力地吆喝。
“人满了,人满了,等一会儿再进。”
这边话音刚落,一辆马车在铺子门口停下,从车上下来几个女眷,管事恭恭敬敬地上前,躬身将她们请了进去。
这些个场面,大家早就司空见惯。
“看看这马车,就知道一出手必定要买不少,自然先让人家进去挑选。”
“不知道新铺子里的布帛比老铺子便宜多少?”
“价钱别太高就行,只想买匹新花样的,给家中老小做衣衫。”
众人议论着,就听到门口伙计传报。
“八匹罗、缎。”
“双色绮出清了。”
还等着买绮布的人登时一阵失望,恐怕今天要白来了。
“一会儿再进去看看,有别的花色的也好。”
攒了银钱,只想在年关买匹好布,刚好赶上坊市打开,听说新开张的布店价钱便宜些,于是早早就来等着,没想到那么快就卖光了。
“不是没有绮布了,就是每日只能卖二十匹,想要买,明日一早再来。”
陈三娘听着门口伙计回应,心中一喜,不禁道:“我只要一匹,卖给我一匹就好,我们一早就在坊门口等着,已经站了快一个时辰。”
伙计乜了她一眼:“别说一匹,就是你要一百匹那也是没有的。”
引来几个伙计一同失笑。
大约是意识到此时这般有些欠妥,伙计咳嗽一声,脸上重新挂上笑容,继续招揽着生意。
陈三娘终于走进铺子,走了一圈,一匹布比老铺子便宜十几文钱。
掌柜还在一旁道:“往年这时候布帛都涨价了,也就是遇到东家新开铺子,才能有这样的价钱。莫要再犹豫,早些买了回家,也能早些做新衣。”
还以为新铺子能如何,摆着的布帛都是从前的旧货。陈三娘去了好几次东市的铺子,怎么能看不出来?
就少了十几文……
陈三娘一阵犹豫,还是决定不买。
“大名府的布帛铺子,也就我们家的最好。”
这也是事实,只不过心中多多少少不舒坦,与其在这里买,还不如去老铺子。
感觉自己白走了一趟,陈三娘心里也是一片冰凉,一双手更是冻僵了,急匆匆地就要往家里跑。
低头才走了一段路,就发现不远处烟气蒸腾。冬日里,在外冻了那么久,光是看着这烟气都觉得暖和许多,双脚也下意识地向那边走去。
走近了才发现,一间小铺子外聚集了不少人。
小铺子支开的窗户向外冒着热气,外面摆着几个奇怪的小炉子,小炉子里应该是烧着炭火,上面放置的陶锅热水翻滚,聚在周围的人正拿着瓷碗从锅里舀水喝。
陈三娘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,就听一个年长些的妇人道:“新开的米行也是,价钱虽然便宜,卖的都是去年的陈米。
“谢家的老铺子米价也涨了,听说过几日价钱还要高一些。”
“这不是逼着我们在新铺子里买陈米吗?”
“那能怎么办?从前还说坊市打开,新铺子多了,兴许价钱能低些。”
“想什么呢?不管是东西两市,还是坊内,都是他家的铺子,怎么可能降价,这进入大名府的米商,都得听谢家的。”
陈三娘听到这里,也走上前去,下意识将冻僵的手伸出来,凑近面前的泥炉,热气登时熨帖着她的手心,让她舒服一些。
“来,我给陶锅里再添些水。”
一个声音从众人背后响起,郑氏带着几个妇人走过来。
聚在这里的人,脸上纷纷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。
她们在新开的铺子外凑热闹,结果发现卖的东西并不便宜,丧气地往回走时,就被这铺子冒出的烟气吸引,然后瞧见了摆在外面的泥炉。
还没问铺子是卖什么的,就听门口的妇人笑着道:“可以在泥炉旁暖和一会儿。”
主家都发话了,她们哪有不来的道理?
再说,真的冻得难受。
然后……大家手里就多了瓷碗,可以从陶锅里盛水喝。
热水下肚,快要被冻僵的心又缓了过来,话匣子也打开了。
等了这么久,就是这样个结果,多多少少也会积攒些怨气,只能说城内的商贾太精明。
“他家三嫂子,今天怎么不说话了?”
几个人将目光落在泥炉旁的妇人身上。
董三嫂手里捧着热水,正小口小口的抿着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“她顾着喝热水哩。”
不光是董三嫂,好几个妇人都是如此,今年柴尤其贵,入山砍柴和秸秆入冬烧了大半,眼见就不够用了,不做饭的时候不舍得起火,很多家就算做饭也不过就是应付一顿,其余的时候垫补点冷食了事。
董三嫂一早出来就空着肚子,哪里想到还能讨口热水喝?
“这炉子从前没见过,里面烧的什么?怎么不见烟气?”
董三嫂不敢往炭上去想,炭今日十三文一斤,谁家能将炭炉丢到外面来,烧水给过路的人喝?
说完这些,大家也将注意力放在了这铺子上。
抬起头看到牌匾上写着几个字。
妇人们不怎么识字,趁着郑氏几个还没进屋,年长的婆子开口问:“你们这是什么铺子?”
郑氏笑道:“这是顺通水铺,我们卖热水、熟水。若是谁家不想烧火,每日只要来我们这里打上一桶水回去,如今坊市门不关了,晚上也能过来买水,灌汤婆子、洗脸、烫脚都使得。”
“天冷了,家中的老幼总要喝些热水,常吃冷水身子弱,久了还会染病。”
董三嫂想到整日缩在床上的婆母,立即道:“热水怎么卖?”
郑氏指了指:“这样一桶只要一文钱。”
听到一文钱,陈三娘的眼睛也亮起来:“那……管热吗?”
郑氏一笑,看向身后的铺子:“你们可以来瞧,我们这里卖热水,也卖温水,还有煮好放凉的水。若是走远路来打水,还能喝上一口解渴,那是不收银钱的。”
“东家说了,也能带些炒面,来一碗热水搅开看看,就知晓我们这水到底热不热。”
妇人们听着笑起来,也引来了路过的汉子。
“都在锅里翻腾,哪里能不热呢?”
众人说着,不过董三嫂却想到了另一桩:“打水的,还能来白舀一碗用?”
说到这里有些不好意思,声音小了些:“不是说能试水热不热吗?”
郑氏点头:“能,以后我们常年在外面都会有炉灶,你们只管用那灶上的水,不过不能带来太多人。”
“那是……”董三嫂道,“不能多,只一个人。”
人家是水铺,又不是白舍水给大家的,这一点都清楚,不过东家也真是敞亮,白舍一舀水不多,却也不少了。
郑氏见围着的人多了,接着道:“每日都来取水,两节一结银钱,会更便宜,一文能给两桶。”
谢太后十三岁就杀过人,大梁兵败之后,她手下的冤魂更不计其数,野兽食人就已经够血腥,谢太后却见过人“食”人的情形,她怎么可能会被一个假装凶恶的人吓到?
气势此消彼长,争夺说话的权柄不过就在一瞬间,只要处于下风,就算一个比她高大的人,也照样能被她一把推开。
掌控了局面和话语权,所有人的目光就只能落在她身上。
“夏、秋两税都交完了,开荒不成,只能与人做苦工,豁出性命辛劳一年,却只得些碎石炭,你们也忍了下来,只因手中有良种,外面有世代耕种的田地。”
“这是你们的家乡,你们会在这里伤人?伤了人之后,是进大牢还是外逃?天寒地冻,走不出一日,就要冻死路边。”
石勇的脸色更是难看。“都是勤恳守法的百姓,还想与人逞狠斗凶?”
谢玉琰环视众人:“还是你们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,要以命相搏?”
不等石勇说话,谢玉琰接着道:“没人买碎石炭的时候,尚能忍耐,为何有人上门送银钱,却生出许多敌意?”
“如果我是你,就好好想想这些。”
“到底是我咄咄逼人,还是有人从中挑唆?”
石勇下意识地向村民中看去,目光落在一个黑瘦矮小的身影上,那人缩了缩脖子,面上一抹惊惧没来得及遮掩干净。
如同一记惊雷在石勇头上炸开。
艰难的时候他们都挺了过去,怎么偏偏在一切有起色的时候,反而与上门的买主生出防备和敌意?
杨家没拿走碎石炭,甚至没与他们立文书,就送来了银钱。
谢娘子也没有仗势欺人,此前来的管事就说过,他们要村中所有的碎石炭,他们私底下有所隐瞒,谢娘子发现问题之后,开口质疑,难道有错?
石勇摇了摇头,他也不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为何会闹到这一步?
谢玉琰道:“骗你们的人,是夺走荒田的人,是那些雇你们挖石炭的商贾,而不是我。”
目光灼热,咄咄逼人,石勇又向后退了一步,眼睛中闪烁出几分羞惭。
谢玉琰接着道:“我有言在前,要将你们村中所有的碎石炭都买走,你们可以不卖,但不该又想赚银钱,又想有所保留。”
“拿更多银钱之前,先想想自己能不能护得住?财帛这些东西,人人都想要,但你也得看清楚,那是真正的银钱,还是灾祸?”
听到“灾祸”两个字,村中人都齐齐色变。
谢玉琰神情重新变得淡然:“碎石炭你们是卖还是不卖?”
最后一句,也是三河村今年冬日最后一个机会。
石勇知道只要他说“不卖”,这位谢娘子立即就会带人离开,从此之后不会再来三河村。
石勇低下了头,闷声说了一句:“卖。”
谢玉琰却没有应声,而是抬眼看向他。
石勇觉得自己的心思全都被看穿,他看了看村子,带头向前走去。走到村南的一处院子,石勇一把推开了院门,生怕谢娘子生疑似的,他指向屋子: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石炭,向下挖了挖,应该有不少……”
石勇喉头滚动:“我是怕又被骗了,留下一些算是退路。也是起了贪心,想着碎石炭卖好了,价钱就会更高,我们到时再卖剩余的,还能多赚些银钱。”
谢玉琰径直走进屋中,看到了地上被挖出的坑洞。坑并不大,只能容一人进出,深也不过五尺,周围土地发黑,显然为了好挖掘,事先烧过地面。
于妈妈上前仔细查看:“应该是这两日挖的。”
谢玉琰看向石勇:“就这一处?”
石勇道:“就这个,这是才发现的,我们挖了一整夜,就弄成这个样子。”
“是谁发现的?”
听得谢玉琰这话,人群中的矮小汉子向后退去,却刚走了两步,就被石勇上前一把扯住。
谢玉琰并不意外,也不向那汉子问话,而是道:“找个大些的地方,村中各户出一人,我们一同说说这笔买卖。”
……
一刻钟的功夫,村民们凑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凳子。
谢玉琰坐在长条凳上,石勇只让村中年长的人跟着一同坐下,其余人都站立在一旁。
那黑瘦矮小的汉子则被众人围在中间。汉子额上满是汗水,脸上露出几分惊恐的神情,他紧紧攥着手,不敢抬头去看那位谢娘子,嘴唇蠕动着,思量着会被问起什么,他要怎么回应。
汗从两鬓滴落,他感觉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他瞧。
石勇看向于妈妈:“昨天管事刚走,赵山就与我说,他挖耗子窝的时候,挖出了石炭。”
谢玉琰道:“如果我不来与你们做这笔买卖,那屋子里还能不能挖出石炭?”
石勇转头去看赵山。
赵山捏紧了手。
谢玉琰很快给了他答案:“能,不过要等到冬日过去之后,在春夏的时候最好。”
赵山听到这话,不禁打了个冷颤,豁然抬起头来,眼睛中的恐惧更深了些。
谢娘子都知晓了,她定是查到了那商贾,那商贾将他供述了出去。
赵山的模样众人都看在眼里,石勇咬紧牙,恨不得立即将赵山按住问个清楚,但他们都知晓,现在这里主事的是谢娘子,他们都要听谢娘子的。
谢玉琰道:“那会儿你们刚刚耕种完田地,朝廷眼看就要收夏税,手中没有银钱,刚好挖石炭来卖。”
石勇听到这里,不觉得哪里不对,在村中发现了石炭,他们定会去挖,而且这次要多挖些,悄悄去卖,免得再被人夺走了田地。
谢玉琰接着道:“挖的深些,就能挖出大块石炭,那种石炭才是商贾最愿意要的。”
石勇点头,跟着商贾挖了一年多的石炭,什么样的石炭最好卖,怎么挖更容易,他都牢记于心。
谢玉琰淡淡地道:“那你们知不知道,矿坑挖深了会冒出毒烟?处置不当就会炸开?”
石勇愣在那里,村中的汉子也互相看了看,脸上都是茫然的神情。
“矿坑炸开,周围的房屋都要倒塌。”
“就算遇不到毒烟,矿坑不稳固、遇到雨季、挖到地下水,任何一样,都能将你们置于死地。”
“即便你们再三小心,也会有人故意让这样的事发生。”
谢玉琰道:“出了这样的事,就算有人能侥幸逃生,朝廷有法度,不允许私自采矿,活下来的人一样要入大狱,三河村的壮劳力都没了,剩下一些老弱妇孺能维持多久?”
“等到整个村子都不复存在,就会有人趁机侵吞村中土地和田亩。”
村民们即便其中有些地方没听明白,但谢玉琰说到最后,他们脸上也露出惊恐的神情。
人在真正害怕的时候,是不会发出声音的。
屋子里一片静寂。
谢娘子说的是真的,那些商贾能做出这样的事。
即便朝廷去查,也是因为他们私自挖矿,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
没有人会可怜他们,为他们伸冤。
相反的,那些得到他们田地的人,却没有任何错处。
这就是为何谢娘子说,银钱也是灾祸……
谢玉琰接着道:“我买碎石炭,是要用来做藕炭,外面传言都说碎石炭有毒,我们卖之前也该好好试一试,碎石炭到底有没有毒性。”
石勇不知晓谢娘子为何突然提及藕炭,但是谢娘子下一句话,就让他彻底明白了。
谢玉琰道:“谁愿意来试?”
短暂的迷茫后,屋子里一双双眼睛纷纷投向了赵山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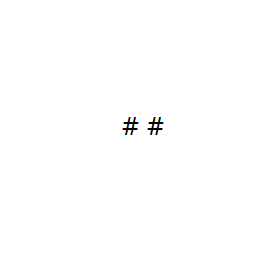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